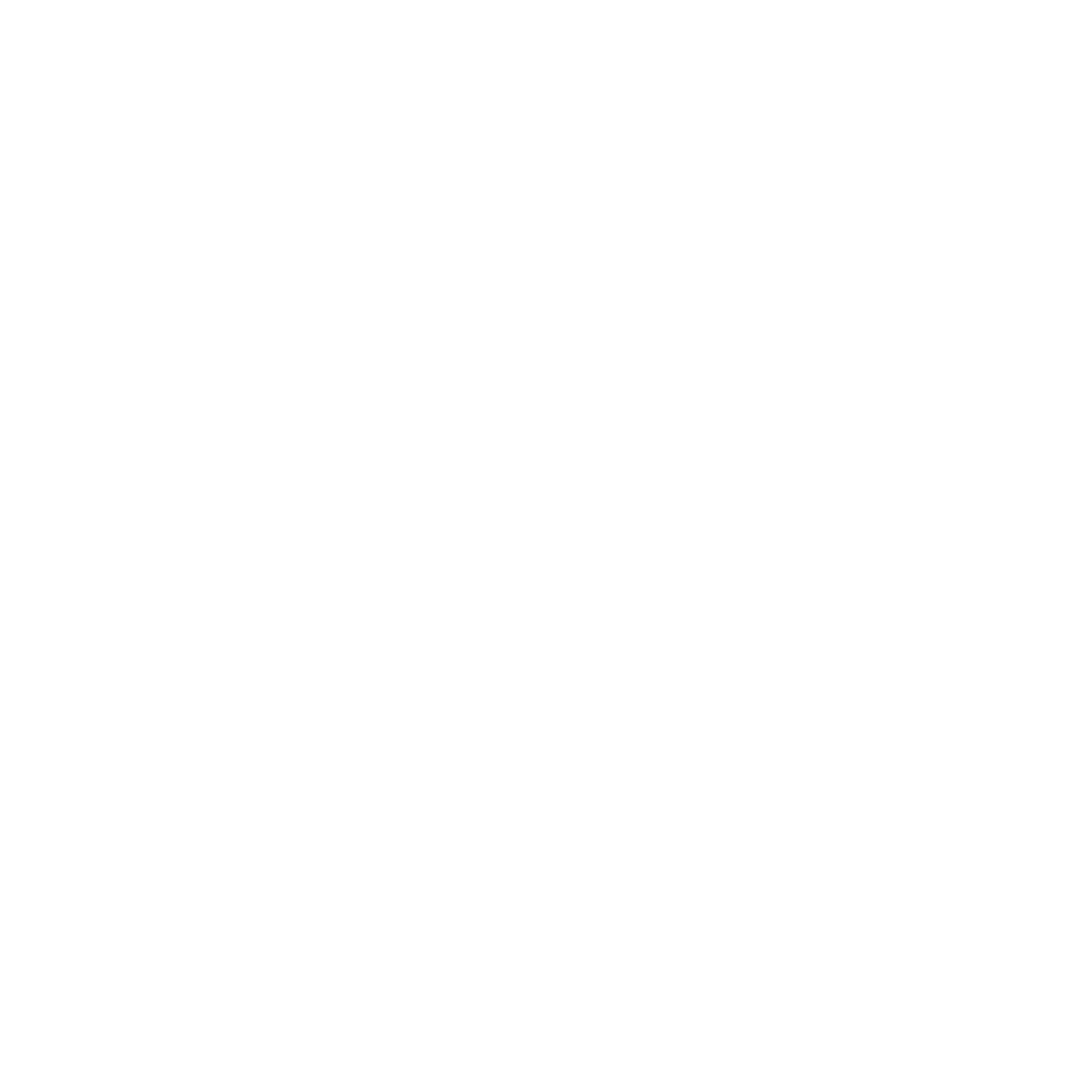甘洲
已经
三变
天圣四年丙寅岁,甘洲大水,洪雾奔冲,赤华林以下数千家卷地而空。以故人家皆移居南岸,梢通南港,岁益久深,自堘之外,不复有人家矣。惟留甃石高一二丈,常泊海舟,今有六十岁人犹见之。
第一部分 家园
第一章
母亲说她以前八十斤,怀我以后每月涨十斤,快过年去做产检,医生说不能这么吃了,她就保持在一百六。手术刀割下去,肚皮厚得割不出血,油溅到副手脸上,副手也怀孕八个月,腥吐了,缝合的时候只剩下医生一个人,肥肉游走,花了两个小时才缝好。我躺在小床上,脐带剪了。医生量过,七斤半,取走我脚底一滴血。几根头发很长,脸是酱油色,指甲在脸上划出吓人的印子。姑姑歪头看我,话不出整句,乌啊,血气,小眼睛,一路小跑走了,带回来一把指甲钳,握在手心里,一块搓衣板夹在胳膊底下。九七年搬进大厦的时候,一对竹竿先进门,后来一根跌下楼去摔断了,九九年又重新凑出一对。家里没有阳台,把两根竹竿从母亲的新窗户,架到附五楼的棚顶上。四楼的人常看见我家晒口罩里的纱布。松青从房间看过来,和母亲讲,阿厘,厨房的烟会飘上来,把小孩子衣服搞得油蒙蒙。于是竹竿又从父亲的窗户搭到房务中心的八角窗台。那竹竿晒过太重的衣服,等我满一岁,已经拗得发青发白,年寿将尽了。我生在九九年,盛夏之初,小名阿㝹。阿嫲是仙游人,怕男孩子养不大,叫我「阿告」。奶奶翻了字典,问了先生,选了几个号名,都不满意,还叫我阿命。这些名字不好听,十岁前有人问我,我都是照父母那样介绍自己,我是甘洲大厦的阿㝹。
依公打假三,自摸一块,一张花牌五毛,有时一天去掉三四百块。他走时,电话穿过十几条街,打到小卖铺,邻居从四楼喊下来,奶奶往上看着,愣了一会儿。邻居把窗户开得更大:依亲!她这才飞跑起来,布包横着,鱼露酱醋一瓶瓶滚出来。她双臂摆得呼呼作响,想过日子,一锅水,三种饭。她跑到,依公躺在地上,已经过去了。她喘口气,摸他口袋,里面有余——六十块钱——竟然还有三百斤粮票。过一会儿她问,看牌,输了还是和了。众人去瞧,全倒在一块了。三轮车载依公到医院去,硬邦邦的,往下出溜。医生说了,人刚刚走,快带走吧。父亲说,医生,请你救救他。医生说,死在这里,就要留下。父亲说,没办法了。行人看着他,他背着他父亲走。依公个子不高,一米七一,人死了,特别重。他背着他从医院出来,从新权路到古田路,过五一广场,看到于山堂。他想起他父亲说,甘洲解放时,这里是公共体育场,有次警报拉响,轰炸机低空而来,他躲到看台底下。国民党轰炸台江,广场上燃着熊熊大火,他躲在那里,整壶茶倒进肚子里,决定要去当兵,报仇十年不晚。他们顺着广达路一路北上,上楼梯时他实在背不动了,父亲停下来,头歪在楼道的水泥墙上。他想到以后,豉酱咸鱼此类不可再食,或许母亲知晓,还是这样推了父亲去死。还有就是,以后,要想办法买一辆车,挂一块体面的车牌,急时好用。
大伯跑回来吃丧饭,上路前订了一口水晶棺,一下巴士就给抓了。他的故事谁也不提,怎么问也问不出来。奶奶考虑了很久,没有搬家。一开始邻居会很仔细地问,你大儿子去哪里了?后来看她不太讲话,就没人再问了。依强是台江第一个大学生,八九年毕业,第二批去深圳,管长江上的巨型货轮。父亲指给我,一栋山蓝色的大厦倒在黑色甲板上,身后是暗淡的夜幕,右尖烧起砖红色的云来。他在深圳成了家,生了个女儿,取一个越字,和恣肆不一样,只一个字。他女儿会夜哭,夜哭时梦游。她梦游不会从窗子跳出去,只是一个人走到浴室里,光脚踩在瓷砖上。她哭像呼出一声声音调平平的气,高一声,低一声,额头皱成一团,胸膛呜呜振响。她被送来大厦以前没人知道,是母亲头天晚上听见了。奶奶说,她母亲怀孕时,大伯上下半夜叫三个女人回家,折磨她,她挺着大肚子,在地上打滚,所以生出来,是这样一个小孩。
大伯从前回来甘洲,西装袖子里露出白袖子,别两个玉的袖扣。他开派对都在楼顶,大厦屋顶,他开水阀,漫天热水洒下来,笑它们落到人们脸上的时候。他们兄妹三个,大伯书念得好,最受疼爱。不好的都是我父亲。小时候同样一件新衣服,他出去三两下就破了好几个窟窿,缝也缝不起来。奶奶抓他来打。有个叔公,一直没老婆,向奶奶讨一个儿子去,爷爷常年跟着部队做饭,他每天来家里洗澡,看到奶奶进屋,就把浴巾掉在地上,跳开一尺,手里掩着下体。这般数回。大伯要念大学去了,奶奶有天做了一顿好饭,煮父亲最爱吃的粉干,与他说,你六三年生的,属兔不属蛇。她舀一小勺海蛎到父亲碗里,说,你一去就补他的位子,赚了工资交给我。你还是我儿子。姑姑说,你爸是个凶狠的人。她小学时,他在路上堵她,抓住她的辫子,在石头路上摔她的头。她停了一会儿,又说,太狠了。你爸是个可怜人。
依姑把初中念完以后,在华联商厦卖体育用品。九十年代,她穿一身黑边波浪领的白纱裤装,眉毛做成半永久的,钱数得哗响。她数钱不用点口水,右手三根手指捏牢,钱顺着左边掌中刮到指尖,再往柜台上笃笃两下,就能告诉你,叁仟叁佰叁拾元,刮风下雨不会错的。依姑有个相好,是个蛇头,留个小胡子,臂膊精瘦,他是萍姐手下的人。他跟依姑好了以后,就把房子卖了,到甘洲大厦开一个双人房,一六〇一。他每次来,一进门就给肆哥五十美元,后来我出生了,给我们一人五十。他喜欢竹荪番鸭线面,每次只吃一子半。他拿一把大剪刀,咔一声,一剪两半,碎屑拢进碗里,说,你称一称,这两半,这次不贪,下回不欠。他说萍姐是仗义的女菩萨,海上漂流的她不做,他因而很敬佩她。又说,两百多人一起,盐水洗澡,盐水刷牙,皮肤和牙龈都裂了,还要吃铁锈一样的红米饭,很苦啊,命都要丢了。金旅号抢滩的时候,他就在船上,是一个渡客。有人跳船,不想交钱,海水漆黑又冰冷,看得他大叫起来。突然,皇后港的灯全暗下去,束束光射过来,飞机迫近,螺旋桨声。那时的蛇头大声地喊,跳,快跳。跳到海里就到了美国,游到底就是自由的海岸!讲到这儿,他就停下来,说后面的不提了。他说,再跑几趟,我就留在纽约,穿西装,戴手表,拿报纸包一把长刀,再也不回来了。我给你买张机票,国内那半我送给你,孝敬老父老母,国外那半,照十年前给你,万八美金,我们往波士顿去,从那里再去哪里,你来决定。那蛇头在大厦住了大半年,后来没钱了,先找总台赊,又找我父亲借了两千。九九年六月有一天,齐蔚告诉我母亲,那人悄悄地退房了。临走前,他拿圆珠笔,在座机旁的墙纸上写,接通天地线。
大伯九八年底开始逃亡,把钱大笔大笔寄往海外,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姑父手上。他九四年漂洋过海,一个月的水粮掰成三个月来吃,几乎死去。镅姊九五年出生,从来没见过她父亲。那场婚礼盛大又漫长,从头天早上四点到第二天破晓,父亲开的头车,吐了几次,稍微清醒一点,又开车把宾客送走。婚礼在甘洲大厦的宴会厅,摆了四十五桌,每个包厢的门都打开,又十五桌。木地板上铺一层暗红染金的海棠花地毯,上面再一条崭新的正红薄毯,细细长长,从大堂台阶下,到厅尽头的舞台边。天花板上六盏水晶吊灯全部打开,男人们跳起来打它们垂下的吊坠,影子晃着。厅对角的两颗迪斯科球,没有光射向它们,这里已经亮得使人发昏了。姑父穿一身天鹅绒面料的孔雀绿西装,笔挺浆硬,胸前别一朵红玫瑰,玫瑰谢完了,婚礼就可以结束了。爷爷已走,没人扶着依姑进来,她一开始就下到场子里,眼睛笑成一弯,中间吐出一点亮光。她穿一身香港定来的长裙长袖,绸面的嫁衣,刚烫的头发氤着药水气味。她唇色鲜红,讲到兴起,拍自己白皑皑的肚皮,背后彩带从这头拉到那头。聊天被烟掩住,听不清在说些什么。人们知道是开心的话、俏皮的话,就豪爽地笑,若说起差点死在海上的事,新郎新娘先后落下眼泪来,大家就揽过他们的肩膀。母亲一手牵着镅姊,一手推着我来。镅姊从小就长得漂亮,像极了她父亲。她一双大眼睛会说话,睫毛长得翘起来。她一盯着你,你就会拿出钞票,塞进她拳头里。那天警察也来,把我父亲带到一边,盘问他。父亲是这样回答:依云自己赚的钱,每一分都滴着血汗。你们不要来坏我们的好事。
姑父这次出去,坐飞机先到法兰西,在波士顿降落。顺利的话,返证有效,他就坐大巴去纽约,再找最便宜的路到迈阿密去。大伯是四月底被抓的,爷爷的葬礼也是四月底,他千难万险回来不是为了这二事。九八年我母亲怀孕的时候,父亲去找姑姑借了一把柜台的枪。她问,哪种型号?他说,折叠式的吧,能装〇点三八米厘的铅弹。你做什么?她把枪拿出来。父亲说,打麻雀去。她把枪一把按住,说,那我不借给你。他这时候才开始察觉,妻子与妹妹陷入了一场对峙。她还煮她的饭,她也给她买漂亮的夹克,只是她们从前会一起去泡温泉,带上镅姊,现在她只说,你皮肤太细,水要把你烫坏了。她们开始在我父亲面前道对方不是。一个说,她以为自己活在童话里,要穿亮晶晶的鞋。一个说,她背叛爱她的男人,你看吧,她那么狠心,会丢下自己的女儿不管。父亲自觉管不了女人的事,拿这把枪,晚上下班到新甸去打小鸟,还去池塘边打鱼,打老鼠。当然,这些他捞不起来,也没有去捡。他跟哗啦和周军一起去,拿五号的手电往树上一照,鸟都不敢飞,有时一个晚上可以打几十头,他们一分为三。麻雀汤色清,味清,骨头酥软,可以咬进去,给孩子补脑,这是最好的东西,他们是这样想。
依姑在一个深夜飞走了。她打包行李时说,我把阿命带走吧,到了那里,抱着小孩,护照撕了,扔在机场,避难去了。她作势要把我的小衣服也包起来,见我母亲转头去给她煎饭团,她也觉得无趣,把衣服又叠好放回去了。她说,她没见过那么多钱,一箱,一箱,又一箱。大伯拿来的钱,她一扎一扎地点过,从天黑点到天亮,一个房间里铺天盖地都是钱,门打不开了,是钱挡住了门。她看着父亲的眼睛说,我不能再回到从前的生活里去了。凌晨两点,她拧开我家的绿铁门,一只手拉起她的皮箱子。镅姊从房间里冲出来。她还没五岁,够不到蚊帐的拉链,她上床之前藏一把剪刀在身上,那把剪刀是纯金的手柄,很沉。她从侧面剪开帐纱,嘭地撞到门上,她跑出来,在沙发转弯的时候一个踉跄,牙齿磕在大理石的地板上,剪刀往前飞去,比她先到了门口。她继续跑,脚趾踩到刀尖上,眼睛睁得很大,抿紧了嘴,眼泪从眼眶正中掉下来,最后她赤脚来到门前的尼龙地毯上。
她母亲在五楼大门一转,往三楼电梯下去了。
姑姑走了一个月以后,我们家里多了一部电话,银色的背壳,洁白的底座和面板,一块小小的屏幕发出绿色的亮光。这电话每天都响,一个月的电话费是母亲两个月的工资。镅姊有时抱着那电话吃午饭,乱按就拨出去。后来父亲把它放在鱼缸上,越姊和肆哥会偷偷把它拿下来,给镅姊,但警告她,你抱着,那边会打过来。从那时起,我们四个就在一起了。
我出生以前的事情,千头万绪,不知是哪头挑起哪头,也不知要引向何处去。母亲的肚子愈合了,留下一道灰色的疤痕,摸起来光滑又坚硬。我拥有非常令人骄傲的童年,父亲母亲都疼我。我喜欢蓝色,一盒水彩笔买回来,别的颜色未动,蓝色那支已吱吱嘎嘎涂不出来了,他们又给再买新一盒回来。母亲总给我作女孩子打扮,一水青蓝色的碎花小洋裙,头上夹五六个小发卡,下巴尖尖的,棋子黑的瞳仁警敏又有神。父亲手巧,小时候自己做弹弓,或者去敲人家的瓦片,钻个洞,磨圆了用竹签穿起来,做成陀螺。爷爷赚四十五块钱养全家人的年代,他用竹子做水枪,龙眼核雕水桶,用宽阔的大衣纽扣做呆头呆脑、转个不停的风火轮。我会盯着他笑以后,他给我做了一把链条枪,拿蓝色铁线拗枪架、扳机和枪针,然后把自行车链条一节一节脱下来,十个一串,前面两截用铜的辐条螺帽敲在一起,做引信头,九号铁线打个活结,可以拖出来,最后牛皮筋缠上,火柴上膛,拉,砰地发出一声巨响。
我家没有阳台,也没有电梯可以坐上来,七十几平米,一共两个房间。家里采光很好,三面都有窗户,早上光在卧室,中午就换到客厅和厨房。房子的挑高有三米六,但天花板离地只有三米,很薄,小时候我拿球去砸,听出来的。客厅的地板是大理石,回南天浸水,缝隙和板面都变得更深。母亲说客厅本来要铺木地板,父亲说卧室本来要铺大理石,都说对方坚决不肯。从铁门一进来跟客厅之间隔着台玻璃屏风,背面是个酒柜,里面塞满了茶叶。来客喝黄龙袍的水仙,懂行的金佛,贵客剑指樱花,最里边藏一包雀舌裹起来的秘茶,来自一棵母树,从岩壁上一摘下来就要送去当官家。酒柜上层只有一个茶杯,盏色乌兰,里布日月食之曜环。我父亲自己喝茶,用一个红鹧鸪斑,后来被我摔缺了一块,他换成一个釉色晶莹、青黑疏密的兔毫盏,初沸的水冲下去,新雪落下红丝磑,他很喜欢,一直用到今天。直到我离开家,酒柜里都没有再添曜变,上层空的位置后来被一些酒填满,茶叶来来去去不见少,我父亲向来没什么客人。找我母亲的人多,秀珠、马丁、敏华、宗亮,都是南平来的。我的名字就是马丁取的,母亲有一本札记写到她,说她有次听到她母亲说,太累了,上班打瞌睡。她吓坏了,把一本字典翻得脱页,生怕再不能去学校了。她对很多事领悟很慢,刚开学都不及格,要用比别人多的努力,到后边才渐入佳境,考个全班第一。我刚出生的时候,马丁来看我,想认我做干儿子,父亲不肯,说她童年青春、爱情子女,全错过了,不知道什么样叫刚刚好,是一个没福气的女人。她戴上花镜,翻了几夜字典,最后合上本子,说,我决定取一个翛字,无牵挂的样子,借庄子美意。南平一中英俄分流,秀珠是俄语班混得最有头脸的,先在二级站卖电器,再后来做男装起家,开涮涮锅,朋友来吃都不许掏钱。她要我叫她宋姨,因为她不喜欢自己的名字,高考填志愿的时候还报了自己新起的一个,自然是不作数。母亲那群朋友,都是因为喜欢看书走在一起。我小学的时候写小诗,现在看来是童谣,母亲全拿给宋姨看,她总不置可否,转头又泡咖啡去了。母亲做月子的时候,她来我家,看了看四周,平平白白的粉刷墙,唯一起眼的就是电视柜上两个掏空的装饰音响,还有左边音响上一个青绿色的铁盘。她与母亲说,下次送点字画来。父亲从厨房走出来,从母亲床底下拉出一幅武先生的字,火燎似的挂上,是李白的诗,最右「君不见」三字最大,盘虬卧龙,而后的全都纠乱缠斗在一起,不好辨识,挥洒隐去了。
我幼时黏着母亲,一秒钟也不肯离开她。她去洗澡的时候,我一定会坐在浴室地上,她一拉上浴帘,我就以为她不见了,大哭起来。母亲带我做菜,看我总想伸手摸厨房那个滚烫的铁锅,于是买来一块磁性画板。她根本不会画画,每天给我画厨房里的事物,却惟妙惟肖,高压锅,灶台,煤气罐,料理台上横一根长杆,上面悬着打蛋器、刨丝板、沥网勺、铁汤勺,最右边两块砧板,生熟分开,跟厨房里一模一样,除了没有那些一把一把从小到大排列的刀。母亲每天都要给我画,画了又擦掉,我也舍得,觉得她下次一定画得更好。她甚至买来一整排厨房用品的冰箱贴,那些迷你的金色勺铲,圆的方的,插在黑色的塑料柄握里,在冰箱上一直待到磁力失效,环扣锈断,掉到地板上。我六个月喊了第一个字。「妈」。因而八个月扶墙走路的时候,父亲总站在我背后。我很喜欢跟母亲一起出门,但到菜市场门口,总不肯进去。在我会走路之后,我终于能看清地面上横流的菜叶和血水,我每次都摇摇头,站在入口,意思是,我在这里等你。我爱干净像父亲,他一天给我洗三次澡,身上不能有一滴汗。他手大,能托住我的头,把身子放在手臂上,母亲出了月子有次也这样给我洗,把我摔进了水盆里,好在父亲手快,在我睁眼前把我捞了起来。但有时他会浑身恶臭地回来,张开嘴,屏住呼吸,让我闻闻他的酒气。他吐得家里到处都是,或者把客厅窗户打开,往楼下吐。吐完了,他清醒一点,就说,要吃我给他做的菜,又接下去很骄傲地说,市场的人都叫我小领导,他们最有人生经验,看相最准。然后他会把我的头扬起来,掐着我的下巴,说,你要离厨房远远的,你看看餐厅的东珍阿姨,脸被酒精炉给烧了,补好了,这里都是皱巴巴的。
断奶时,母亲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送去南平阿嫲家。母亲从来不买衣服,从小到大衣服都是北京亲戚退下来的,崭新,全是从香港买来的。但她那天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连衣敞口裤,披一条白底泼墨的丝巾,连衣裤是她新买的。到了南平把我放下,母亲给我一张纸,上面有十六个格子,说一天涂一个,涂完了她就来接我。第一天晚上,阿嫲抱着我站在厨房窗口,面前是一座高耸的广告塔,往四面八方抛下海报,顶上露出昏黄的光,把海报上的男男女女照得眼窝深陷。阿嫲家在省二建的坡上,所有拉木材的车都要爬上来,或者溜下去,发出隆隆巨响。我指指停在坡下的一个三轮车夫,意思是,我要坐人力车回家。阿嫲说,这里是高坡,他骑上来命会送掉。第二天,我拿一把圆珠笔,细细密密地把剩下十五个格子一下子涂满了,我闭上眼睛,又睁开,然后跑到水泥阳台,透过最下面一个孔往外看看,母亲没有从大石头台阶走上来。我只好拿起那台红色的座机,拨我偷偷记下的母亲的电话,八,七,八,〇,五,四,六,八。听筒按得我耳骨生疼。没有通。我知道另外一个号码,很短,五,〇,〇。我心想,嘟一声,一定有人接起来,然后会听见母亲轻咳一声。还是没有通。我把电话合上,过了一会儿再把这两个号码打过好几遍,可听筒像坏掉了一样,只有一点点嘶嘶声。我最后一次放下听筒,想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,我脖子通红,把那台电话摔在地上。
十六天后母亲来接我,撩开木门外的小熊布帘,轻轻地迈进厨房里。阿嫲的厨房和客厅是同一块地方,一共不到十五平方,摆着一张切掉一半的圆桌,还有一架缝纫机,面上都粘着黏黏的油雾,做锅边时柴火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我在阳台的摇椅上躺着,猛地听见一个穿纱裙和波跟的女人,裙摆擦过水泥墙面,在一张高凳上坐下来。我扶着门框,矮床,阿嬷的古董撒帐床架,床架上的玻璃窗,又一个门框,一小步一小步走到厨房,看见这个人穿一件草绿色的夏衣,墨荷印的百褶裙,一头短发扎起来,背着我和阿嫲说话。我没认出她是谁。我看了好一会儿,仰起头,怯怯地叫她。「妈妈?」这时她激动地回过头来。她在窗口坐了太久,雨打湿了她的脚踝。
母亲每天给我读书,教我写简单的字。那些字我写着写着,会左右颠倒,上下笔划分成一个一个零件,被我重新组装在一起。我开始能用言语描述周围的世界,看见电饭煲里升起的白烟,说「烫」,看见歌手唱到动情,说「喉结」。但是过了很久,母亲发现我还不会讲三个字,她担心我一辈子都只能用两个字说话,带我去看了医生,没有结论。直到有一天,母亲又一次给我读一本图画书,读到红棕漆皮的时候停下来,想了又想,我接下去,斑斑驳驳。母亲大叫一声,高兴得亲我的脸颊。在托儿所,老师让我们讲故事。有的孩子已经会用动物讲简单的童话,有的孩子还说不出句子。我说,有个屠夫,金银财宝装在铁匣子里给人偷走了,他老婆在大哭,他在大笑。他老婆说,匣子都被人偷走了,你还笑什么。他说,钥匙还在我这里咴。我看老师不作声,又说,我外公可以空手抓老鼠,所以他不喜欢猫。有次猫吃了梁上挂的肉,他抓着木棒要打死它。后来老师也说故事,让我们回家复述给父母听,那些故事,我统统不记得了。父亲母亲带我去崭新的华都,路上会在温泉大饭店停一下,走进它又高又广阔的中庭,搭透明的电梯到顶楼,再坐下来。温泉大饭店的大堂比我们气派,从天上垂下来千百个烧得温暖晕黄的钨丝灯泡,金属的栏杆、高耸的绿植,都是暗金色的,白天黑夜,都显得辉煌又灿烂。到了华都我坐在购物车里,有时候也站起来,面对着推我的父亲。父亲一般不会讲故事给我听,他不知道什么故事,也不知道与我有什么可说的。但他还是时常指着一件什么东西,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。很多时候我都抢着喊了出来。渐渐地,我开始有些口齿不清,泥鳅香梨,斯人诗篇。母亲把我送到对面的妇女联合会,上认读学校,警告我,甘洲口音会让我变得和父亲一样「穷苦」,没「自觉」,天天夜夜跳进河里去「游泳」。母亲第二天又给我报了一个画画班,但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次课了,我画来画去就是绿树和红房子,蓝天涂得漫山遍野。我心里知道画得没有别人好,后来就不去了。
有天我梦见,我从客厅的窗户跳出去,像一张画纸,一点点盘旋,飘落在地上。天亮后,鲤鱼洲的地面湿漉漉的,昨夜下了千年来第一场雪。我搬一把小凳子,开始把东西往下扔,遥控器,水彩笔,茶杯,杂志,最后我把那凳子也扔了下去。阿罗在扫地,看着满地碎片,往上看,没有人在窗口。周军去各个科室送报纸,从三楼看下来,盯着地上一只蓝色拖鞋,说,好像是阿㝹的。越姊已经被送去深圳,镅姊搬去和奶奶住,秋天要开学了。母亲回来以后,生气地拍我的头,问我,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说,在做实验。母亲笑了。她走进房间,拿起我最心爱的一个兔子时钟,走回来,拉开纱窗,抱起我,对楼下的人喊,大家注意了。她松开手,那只小钟落下去,撞在程英家的空调上,弹起来,跌进一丛树叶,我以为它要掉进河里,但没有,它啪的一声,摔得粉碎。晚上父亲回来,母亲与他说了此事,父亲说,还在吗?捡回来修一修。说完他跑下楼去,回来时带着那个遥控,拿出一个沾满铅污的工具箱,捣鼓起来。他修好的时候,恣肆回来了,今天他特别沉默。他径直走去浴室。他走过的地方,掉了一地沙子。父亲重重打开浴室门,看见恣肆一条一条把裤子脱下来,里面塞满了沙子。
那晚父亲母亲大吵一架,他们那时都精实健壮,口沫横飞,左右脸颊鼓出一条肌肉,身上每一根血管都成了筋骨。他们指节攥得发白,肚上刀疤同时裂开,滚烫的血喷溅出来。最后他们不知道说起一件什么事,母亲走进厨房,举起那个铁汤勺,像刀一样挥向父亲。父亲拿手臂去挡,勺子在他小臂上刮下淋漓两痕。我站在他身前,勺子要掉下去,他半空中接住。他会向母亲掷回去。他没有,他抡起铁勺,狠狠朝鱼缸砸了下去。
房子里充满了腥味。肆哥站着,身上的沙子已经洗净了。我从碎片里把金鱼捧起来,走回浴室里,学动画片里做的,把鱼放进马桶,看它们打着旋,一口气冲到大海里去了。他们本就分房睡,现在摔上了门。我找一块干的地方坐下。他们都不知道,我坐在地上的时候,心里暗自做了一个决定。
如果他们离婚了,我要跟母亲。